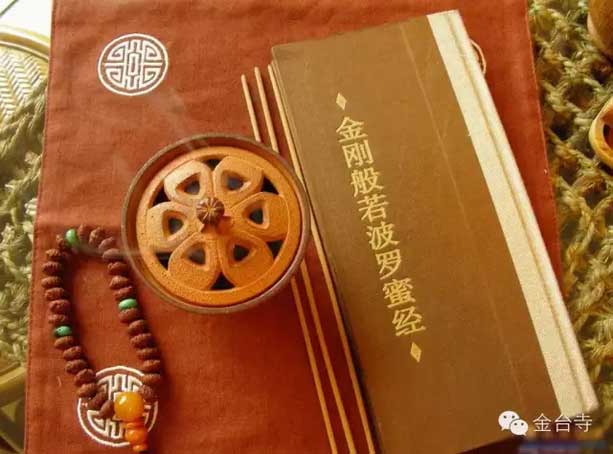
二、印度佛教的变迁
佛教源于印度,此乃众所共知者,传入贵霜帝国后,其王迦贰色迦大力弘扬,乃得大盛,但与此同时,印度本土之婆罗教开始复兴,婆罗门教系印度本土古老宗教,其中若干神祇,佛教兴起后,多予采纳为护法神。印度笈多王朝后期定婆罗门教为国教,诸王先后信奉婆罗门教,以沙姆陀罗笈多及迦摩罗笈多表现最为突出,佛教在印度逐渐衰微,其所以如此,佛教内部有人妄解释迦牟尼的教言,发展出与之相违背的修行方法,掺入败坏风气的双修法,号称密教,严格的说,既已违背释迦牟尼的教法戒律,已经不再是佛教了,大可自立门户另创新教大可不必扛着佛教的招牌,做出释迦所禁止的男女双修的恶行,但是这些创立及奉行密教者,却不肯或不敢放下佛教的名号,依然披着佛教的外衣,以佛教徒自居,因此使印度佛教与婆罗门教本身相较而言,「印度佛教起码有如下不足与缺陷:
第一,佛教僧侣入于密教而生活腐败;
第二,佛教僧侣热衷于文理的空谈,仅在学术中心之地如那烂陀寺等处发展,荒于对民间的深入普及;
第三,佛陀四谛、八正道之教法,对于一般民众不能即闻即知,也不能即知即行,他们于艰苦生活之下,只盼有一个救世主将他们带往快乐的天堂;
第四,佛教四姓平等之说,破坏了婆罗门僧侣的特权。」4
印度佛教被密教掺入后,生活腐败,社会岂能对之有好感,而婆罗门教蓄意复兴已达数百年之久,自是趁密教「搞」垮佛教之际,迎合印度普通民众願望,揉合民间信仰,同时也吸纳了若干佛教的哲理,以新的姿态重新获得印度人的信奉。
4 圣严法师编述《印度佛教传》,福建莆田广化寺印,页 217~218,但此处系转引自克珠群佩主编《西藏佛教史》,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9 年,页 3。
婆罗门教既重新在印度成为主流宗教,於许多印度佛教僧侣包括密教僧众,既难以在印度立足,便纷纷进入今中亚地区,其时中亚地区正盛行琐罗亚斯德教及其后继的摩尼教,摩尼教僧侣(借用此一词汇较易瞭解,事实上摩尼教之教师称慕睹,颇为少见,故仍称之为僧侣),无论琐罗亚斯德教(传入中土后,称之为祅教)、摩尼教,为弘扬其教法,往往掺入许多「幻术」,如吞刀、吐火、开肠破肚等,用以招徕信众,佛教进入中亚(古称西域)后,也染有此种风气,如诸胡列国时(即一般史传所称的五胡十六国,但以其时 304~431 年,既不止五胡,也不止十六国,称之为诸胡列国较为周延),西域胡僧佛图澄(或作浮图澄),就善于幻术,据慧皎《高僧传》载:
「(佛图澄)善诵神咒,能役使鬼物,以蔴油杂胭脂涂掌,千里外事,皆彻见掌中,如对面焉。亦能令洁斋者见。又能聽铃音以言事,无不效力验。」5
佛图澄的「神蹟」,在正史《晋书》上也有如下一段记载:
「(佛图澄自云)百有餘岁,常服气自养,能积日不食,善诵神咒,能役使鬼神,腹旁有一孔,常以絮塞之,每夜读书,则扳絮孔中出光,照於一室;又尝斋时,平旦至流水侧,从腹旁孔中引出五脏六腑洗之,讫,还腹中,……」6
像佛图澄的这些「神奇」行为,已超出常理,一般而言对史料之鉴別,衡诸常理是极重要的方法之一7,即使《高僧传》或《晋书》以白纸黑字录下这些「神蹟」,在衡诸常理下,都属不可信者,充其量只是施术者对旁观者予以催眠后所产生的幻觉或虚像,不可能是真实的。再看稍晚於佛图澄,也是西域高僧鸩摩罗什也曾有吞铁钉之「壮举」8,这些有违常理的举措,显然是受了袄教、摩尼教僧侣善幻术的影响,因此修习幻术以广招信徒,按袄教、摩尼教的传教士(袄教之传教士称祭司,麻葛或穆护)幾乎都精通此等幻术,其在中土弘传其教时,也常以此幻术炫人取信,佛教传入西域后,僧侣习得此等幻术,再带入中土(如佛图澄、鸩摩罗什……等)也就不足为奇,至於所谓密教,其创立之始就崇尚幻术(注意,琐罗亚斯德教、摩尼教都曾传入印度),而这一类幻术都是释迦牟尼教法所不允许的,都溢出了释迦佛教的范畴,只是披着佛教的外衣,其本质上已经背离了佛教。
5 见《高僧传》,北京中华书局,1992 年,页 345。
6 《晋书》卷九十五《佛图澄传》,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。
7 杜维运《史学方法论》自行出版,台北三民书局总经销,1979 年,页 141。
8 《晋书·鸩摩罗什传》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