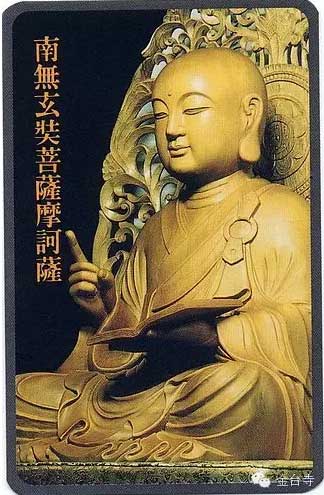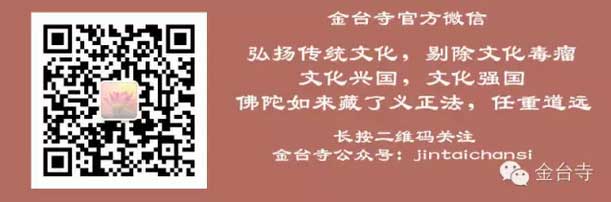| 首页 » » 高僧学者名人批判双身法之西藏密宗(藏传佛教)证据大公开 |
台湾文化大学教授说喇嘛教(一)2 |
密教既然自身演化出炫术,又吸取了袄教、摩尼教的幻术就施行法术这一点看,它更像袄教或摩尼教,摩尼教对于人类性关系「达到了幾乎肆无忌惮的地步(某专书有一段极离奇的乱伦叙述,此处不予赘引)」9,密教中的双修之说或与此有关,其非佛陀本意是极其明白的。自从密教出现后,印度本土几已不见佛教踪影。
上述这扛着佛教招牌的密教在西域传播,德国学者克林凯特曾明白指出: 「……这一点表现在密教的产生,这个教反映了晚期印度佛教的特点。它含有色情成分和令人恐惧的神仙,这也就是構成西藏佛教的主要因素。」10 以上对密教的描述相当深入,试想真正的佛教是戒杀、戒色…慈悲的宗教,怎么可能会「含有色情成分」以及望而令人心生恐惧的「神仙」?而且还会用人的头盖骨、胫骨作成祭器,而这些「就是構成西藏佛教的主要因素」,这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初衷显然相违背。既与佛陀的教义,戒律相左,严格的说已经不是佛教。克林凯特在同书中还指出在西域和闐(按和闐为今日之称谓,古称和闐,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南端今和闐市)巴拉瓦斯特保存有一幅确切无疑是密教的画像,克林凯特对这幅画的判定是: 「是一个大概被看作大黑天的三头神,他阴茎勃起,居中的头顶上有一颗死人头骨,双手分別举着太阳和月亮。这里突出的内容除了做爱之外,就是令人恐怖的东西。」11 这幅画创作时间,大约在西元六至八世纪之间,从克林凯特对这幅画的描述似乎是除了色情与恐怖之外,別无他有。其实这幅画还透露另外一项讯息,在这画像后面的两隻手,右手持月,左手持日,高举日月,这有很浓厚的袄教、摩尼教色彩,这似乎说明密教从袄教、摩尼教吸取养份。当唐武宗李炎会昌年间(西元 841~846 年)禁绝「三夷教」后,摩尼教隐身於道佛两教之中(会昌之后,佛教很快复兴),但其非道、佛两教,其理至明,同理既违背佛教教义与戒律,又采纳其他宗教理论的密教实不宜再宣称自己是佛教。 9 可参看芮传明《东方摩尼教研究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9 年,页 174。 10 德.克林凯特 Hans-Joachin Klimkeit 著,赵崇民译,贾应逸审校《丝绸古道上的文化》,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,1994 年,页 157。 11 见《丝绸古道上的文化》页157~158。 三、吐蕃的宗教 在清朝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之前,均称之为吐蕃,「吐」是后加的,「 蕃 」才是这个民族的本名 。「 蕃 」,在唐以前其读音为「 钵 」、「伯」、「博」,其字根「番」衍生而来的「播」、「皤」、「鄱」……等至今其读音仍近「钵」、「伯」、「博」;「吐」乃汉字「大」在唐以前的读音,「吐蕃」就是大蕃,以示与大唐立於平等地位。其民族自称「蕃」,可能与其传统信仰的「本」教有关12,所谓「本教」只是万物有灵的萨满信仰13,这是举世每一个民族都曾经有过的,即使是今日,这种万物有灵的信仰,仍然存在于许多民族或社会中。吐蕃社会之有萨满信仰乃是极自然之事。 12 此处称「本教」者,乃是采一般既成的说法,事实上信仰与宗教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,自有人类以来,幾乎就有信仰,其历史可追溯距今几万年以至几十万年以前,但宗教距今不过三千多年,信仰的心理基础是:恐惧、感恩、与许愿,此点可从古岩画中寻到证明;但構成宗教则必得有其必备的条件如:自有的经典、自有的神祇、固定的礼拜场所、传统的礼拜仪軐、专业的神职人员,神职人员有其传统的服饰,趋吉避凶,最後审判等八项条件,详见胡耐安《边疆宗教》,蒙藏委员会,1961 年,页 3。对以上八项条件,所谓「本教」并未完全具备。 13 「萨满」乃是西北利亚土著民族对于「巫」的称谓,肃慎系民族也然,初民社会把宇宙看成是立体的,上(天)界为诸神所居,地面界为人及万物(含山川湖泊)所 居,地下界则为魔、鬼所居,「萨满」可与神、鬼沟通,且万物有灵,也赖萨满沟通以为人类祈福消灾。可参看日、护雅夫著、郑钦仁译《匈奴》一文,富育光《萨满教与神话》,辽宁大学出版社,1990。 相传吐蕃在西元七世纪初,其赞普囊日松赞在内乱中被毒杀而死。(吐蕃语称其国家元首为赞普,一如中原称皇帝、匈奴称单于、古埃及称法老、柔然、突厥、蒙古称可汗),由其子松赞乾布(西元596~650 年)嗣立为赞普,此人两《唐书》均作弃宗弄赞,或简称弄赞,嗣位时年仅十三岁,此人统一吐蕃各部,开疆拓土,国力日盛,威震四方,先娶尼泊尔尺尊公主,后闻其东邻吐谷浑娶唐公主14,遂向唐朝请和亲,唐朝时为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未允所请,吐蕃遂率兵东掠唐边境,双方经过一场战争,未分胜负(此为汉文史料所载,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唐军落於下风)。松赞乾布复派使者持厚礼请婚於唐,这次唐太宗允其所请,以宗室女为文成公主嫁吐蕃松赞乾布赞普,时为唐太宗贞观十五年(西元641 年)。因尼泊尔尺尊公主及唐文成公主都笃奉佛教,入藏时都携有佛教及佛经,一般而言佛教开始传入吐蕃,据汉文文献记载,唐太宗在确定文成公主入蕃后,应文成公主之要求,赐予金释迦牟尼神像,十八种工艺书籍,《大医典》、八十部占筮历算法及无数锦缎物品,各种农作物种子,侍女十六名,勇武力士百餘人,在江夏王李道宗护送下入蕃15。尺尊与文成两公主虽将佛像等佛教文物携入吐蕃,但其时吐蕃尚无可资应用的文字,要谈传播佛教,言之尚早。 14 吐谷浑应读作吐浴浑,其统治阶层为鲜卑慕容部,名吐谷浑,初因其所部与嫡弟慕容廆所部斗马而失和,遂率所部数百家西徙,至於今青海一带,至其孙统治当地土著建立政权遂以吐谷浑为国号,故其统治阶层为鲜卑慕容部。 15 克珠群佩主编《西藏佛教史》,页 14。 因此派吞米桑札布到印度学习创制吐蕃文,由于吐蕃文之创制,为吐蕃译经事业奠定了基础,在松赞乾布主导下,不仅大量派遣吐蕃青年到周边邻国学习包括佛教在内的各国文化,而且还相继从唐朝、印度、尼泊尔、克什米尔、波斯等地迎请许多班智达(此是梵语,意为学者,如细究之,则指精通《五明》者的称号)到吐蕃传授知识、翻译各种经典,从而开创吐蕃佛经翻译的新纪元。按唐朝以文成公主嫁吐蕃松赞乾布事在唐太宗贞观十五年(西元 641 年),其时唐三藏法师玄奘已离开高昌,经今中亚西突厥控制下的各国到天竺取经(天竺即印度),其时高昌王为麴文泰,自恃城墙高厚,唐朝距离又远,不可能远道来征,因此妄自尊大不遵臣礼,唐太宗乃於贞观十四年(西元 640 年)派侯君集率大军征讨高昌,灭之,将其地设为西州,自是已与西突厥接壤,但对西域情况所知不多,必须有详细的西域人文、地理资料,恰好玄奘於贞观十九年(西元645年)回到长安,按玄奘之西去东返,都经过西域,亲眼目睹了西域「现况」,而这就是唐太宗亟欲得到的资讯(以现代的话说,就是「情报」),因此对玄奘回到长安,给予极大的欢迎,并要他就经过西域各国的情况写出来,玄奘何等聪明岂会不知道大唐皇帝的真正用意,於是由玄奘口述,经其弟子辩机笔录,完成了一部震烁古今的巨著《大唐西域记》全书十二卷,叙述西域各国地理、历史、人文的只有一卷半,叙述印度佛寺者反多达十捲半,可是书名为《大唐西域记》,这当然让唐太宗龙心大悅,於是拨出地方,提供经费,派出人手,让玄奘大师从事译经工作,一时之间长安成为佛学胜地,这个情形松赞乾布不可能不知道,於是派遣吐蕃青年到长安「留学」,据汉文文献所载,当时松赞乾布令国中豪族: 「释毡裘,袭纨绮,渐慕华风,猜犷日革,至遣子弟入国学而习业焉。」16 这些到长安「留学」的吐蕃青俊,除了研习儒家经典之外,对当时长安一片翻译佛经的气氛,不会不受到感染,极可能学习佛经,也成为其在长安重要课题,学成返回吐蕃,必然把中原的佛教思想带回吐蕃,更可能把一些汉文佛经带回吐蕃,然后译为吐蕃文(在诸胡列国时代,西域胡僧鸩摩罗什在后秦姚兴支持下,曾翻译了许多佛经)。松赞乾布除派遣青俊到长安留学外,也同时礼聘印度、尼布尔等地高僧到吐蕃一则宣佛法,再则翻译佛经,此时所翻译或所宣讲的佛经自然是未经过所谓「密教」加工过的正统佛教经典,也就是不带色情和恐怖成分的佛教。 16 见《册府元黾》卷九七八《外臣部.和亲》,但此处系转引自《西藏佛教史》页27。 佛教在松赞乾布大力推动下,自是有所发展,但吐蕃本土传统的本教信仰根深蒂固难以禁绝,松赞乾布死后,王宫内的宗教信仰又重新回到擅长咒术巫法的本教手中17。其后于松赞乾布玄孙赤松得赞赞普时(此赞普为唐金成公主所生),迎请印度密教莲华生入吐蕃,宣扬密教,并强力打压传统的本教信仰,其时约为西元八世纪中叶,吐蕃的佛教也开始了质变,及至西元 820 年赤祖德赞(或作赤热巴巾)赞普时,更是大力扶植已经开始质变的佛教,也由于其全力压制本教,卒被本教信徒所暗杀,而由其兄朗达玛继任赞普,朗达玛笃奉本教,於是开始展开灭佛措施,其时为西元841 年,说来也巧,唐武宗李炎的禁绝三夷教(佛教、摩尼教、景教)也在此时。一般而言,对吐蕃在朗达玛灭佛之前,称之为吐蕃佛教的前弘期。 朗达玛前后在位六年(841~846 年),也是被刺身亡,他的灭佛作为大致而言有以下几项作法:1、停建、封闭佛寺、停止佛教活动;2、破坏寺院设施;3、迫害和镇压佛教僧侣;4、焚毁佛经,断绝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佛教文化往来18。自朗达玛灭佛之后吐蕃陷入一片混乱,许多佛教僧侣四处逃避,吐蕃文献称之为黑暗时期,一直到西元十世纪之后,情况有了改变。之前外逃的佛教僧侣或逃往今西康一带(中共建政后,撤废西康省,将金沙江以西并入西藏自治区,金沙江以东并入四川省),或逃往印度,仍留在吐蕃地区的佛教僧侣「开始依附于本教的羽翼之下,这有力地促进了佛本融合,通过佛本融合,外来佛教在内容上更加接近以本教为代表的西藏传统宗教」19,这一看法既正确又重要。据传朗达玛灭佛时,其弟毗啰母吉鲁赞皈依佛教,有恢復佛教之志,时他弃国远游印度,师事密教阿底峡(或作阿提沙),朗达玛被刺身亡后,吐蕃人迎立毗啰母吉鲁赞为赞普20,此时先前逃亡印度的僧侣均返回吐蕃,当然也有一批印度密教人士随之而来,同时逃到西康的僧侣也返回吐蕃。吐蕃人对地理方位之解读是把西边阿里一带称为上路,而将东边西康、青海一带称为下路,於是上、下两路僧侣纷纷回到吐蕃中心拉萨一带。 17 见黄国煜《世界宗教》,台中好读出版公司,2009 年,页 231。 18 见《西藏佛教史》页 88~90,另释妙舟《蒙藏佛教史》页 7,也有相同说法,此书系扬州广陵书社出版,2009 年。 19 见《西藏佛教史》页 92,原文本教作「苯教」,此处为求前后行文一致,改作本教。 20 见《蒙藏佛教史》页 7。 【未完,请继续阅读下一栏《台湾文化大学教授说喇嘛教(二)》】 免责声明 本平台所收集的部分公开资料来源于互联网,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,並不代表本平台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,也不構成任何其他建议。本平台部分作品是由网友自主投稿和发布、编辑整理上传,对此类作品仅提供交流平台,不为其版权负责。版权属于原作者,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,请与我们取得联系,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。谢谢!
|
| 首页 |